�@�@����Ъ��ֺq�q�}�l�N�P�S�ӤH���B�ҵL�k���}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Ъ��ֺq���q�¬��S�ӤH���t��§���ҶǤU�Ӫ��ֽg�C�H�C�q���ҡA�L�b�@�̫�@���P�L�����{�E�|�Y���\��u�L�̰ۤF�@���ִN�X�Ө���V�s�h�v�]����26�G30�^�A�̷��ɪ����p�A�L�̩Ұ۪��N�O�ֽg115-118�g�]The Great Hallel�^�C���S�ӤH�ֽg���۪k���T�ءG���q�P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۪k�]Responsorial�^�A�|���θ֯Z������۪k�]Antiphonal�^�A�ε��w�k�]Cantillation�^�Y���q��Ū�g�̨̬Y�DZ۫ߪ������̸g�媺�����H�ۥѪ��t�סu���g�v���覡�C�o�ǰۡ��w�ֽg��Ӽv�T�F������з|���֡A���v�a���L�k�T�����X�S�����Ҥl�ӻ����A���L�̳��۫H�b�o�ǥ��¬��Ǩ��N�з|�����֡]�۫ߡ^�ܦh���P���ЩΥ@�U���q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]Grout 1973: 12�^�C��N�з|�Ǩ�p�ȲӨȨ�D�w�A�Ʀܨ�ڬw�A�P�ˤ]�b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̧l���F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A�ר�b��þ�j�դ�Ƥ��v�T�U�A��ӫ�Ӫ��ڬw�з|���ֲz�׳��O�إߦb���K���z�װ�¦�W�A�o�dz��O���ئ@�@���]Grout 1973: 12-13�^�C
�@�B�ڬw�t�֤����U�ڷ�
�@�@���@���з|��Ambrosian chant �Ϋ�Ӫ�Gregorian
chant�]���b���P���Ҥ������ɥ��q���檺�v�T�ӧΦ����Q�u�����з|���֡C���M�ѩ���L�S�O�V�m���פh�P�֯Z���t�m�A�[�W�@�۫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Φb§���W���t�X�A�ϳo�ǯ��q�@�ئ��@�شX�G�P�@�j���B�R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з|���֡A���ڭ̤]�����o�{���Q�T�@���g��q�]motet�^�o�i�ɴ��A�@�̦p��H�즳���q�D�۫ߤ����q�W�ȩ����]augmentation�^�A�S��@���@�U�����q�]���ɥ]�t�q���^�α۫ߦ����ĤG���A�ۤv�~�[�W�Ч@���ĤT���A�c���@���T�n�����g��q�]��Grout
1973: 98-109, Apel: HAM (I) 1962: 35f,
218f�^�C�o�ظt�B�U���P���q���P�t�U���P���߲۫V�b�@�_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g��q�A�q�ڭ̲{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ݨӦ��G���i��ij�A���̤��@�����DzΡA�@���g��q�ëD�u�@���A�o�����G�B�T�إͩR�G�o�i��䤤���@�ΤG�n���@���W�ۦ��A�Υi�ٲ��Ĥ@�n���A�u�ۤU�G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֤G���ۡA�Υu�H�־��u���ĤG�T���Ӧ��U�֪��W���P�]��O
Mitissima (Quant Voi)-Virgo-Hec dies, Grout 1973:100�^�C
�]��1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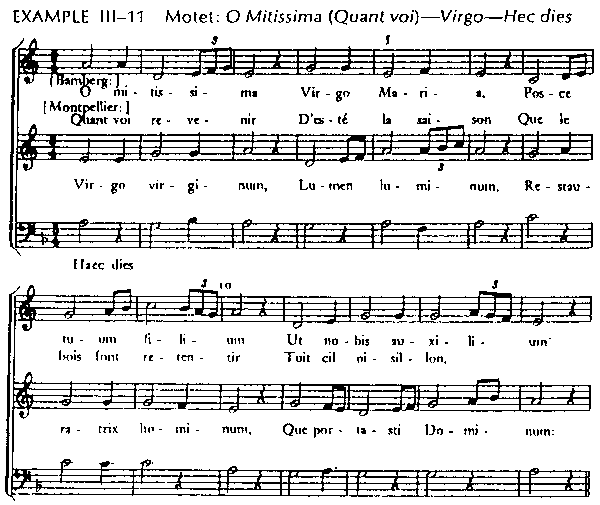
�@�@���B���w�]Martin Luther�^�ﭲ�ɴ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v�Чﭲ�B�ʡA���R�ۺq�������ǵۥ��q���۫ߨӶǹF��ﭲ���иq�A�D�Ĩ����q�ΥH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t�֡A��u�W�ҬO�ڦw���n��v����۫ߴN�O�@�ҡA��LJ. S. Bach�t�M�n���ƭ��t���p��Innsbruck���쬰�@���y��q"Innsbruck�ڤ������A"�A���ɥi���Johann Hesse�]1490-1547�^��s�q����O World, I now must leave thee���]�@�ɡA�ڤ������A�^�Ӧ�����§���t�֡]Young 1993: 509�^�CBach�Ѵ��b�t���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ϥΦh����Passion Chorale��ӧ����u�t�D�Y�B�����ˡv�]Paul Gerhardt,�qLatinĶ���w��^�i���O�w��t�֤��̯��t�P�H���@���A���֯�ƷQ�쥦���ӬO�@�����Hans Leo Hassler�]1601�^�ҧ@���ʪ����q���ڤ߱����ó��]�@����֤k���H�]Young, 1993:526f�F Glover 1990: Vol 1, 289-298�^�C
�@�@20�@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۫P�t�ֺq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̨ΨҤl�O�^��The English Hymnal�]1906�^�����ֽs��Ralph Vaughan Williams���ǧ@�A�䤤�̱`�۪��O�u�j�a�u�B�Q�����֡v�]��O Sing A Song of Bethlehem���AKINGSFOLD�^�Ρ�I Sing the Almighty Power of God���]�ںq�|�W�D�j�v��FOREST GREEN�^�C
�@�@�H�W���|�ƨҦ��b���X�t�֦۩l�N�P�U�a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֦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A�{�b�ڭ̨Ӭݥx�W������ѱз|�����ֱ��Φp��C�]����Ҳo�A���d�Q�C�@�����~�A�ȭ���x�W������ѱз|�A��L�Ь��]�ʥF��ơA�����Q�ס^�C
�G�B�Q�C�@���ǤJ�x�W���ڬw�t��
�@�@1624�~�����H�X�i��F�L�פ��q�Φb���z���ӷ~��a����n�x�W�A��1662�~�Q�G���\���X��37�~���@�@�����F35���k���С]Reformed
Church�^���űЮv�A�HZeelandia�]�x�n�w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i��s��B�¨������H�ڤ��ǹD�C�ڳ��űЮvRobertus Junius
(1629-43)����5900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6400�W�A���}�B�G1965�G2�^�I�~�J�з|�C�L�̤]��]�}�ҡA�оɤj�H�P�p���Ѧr�έI�w����Эn�z�ݵ��C�b1647�~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A�צ��֦~577��Φ��H800��b�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Ш|�]H.
Chen 1947: 26�^�C��1638�~�G�뤭�餧�x����x�]Tayouan Day
Journal�^�O���G�u�K�C��оɤ֦~�̡A�B�аۺq�K�ηs��y�H�ֽg100�g���۫߰ۡy�Dë��P�H�g�z�v�]Campbell 1903:
161�^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b1636�~�����i�]�O���u�bJunius���ͻ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ɤ��U�A�Ǯըk�ĭ̦b���D���e�Τ���ۺq�A�H�̴I�Ш|�ʪ���k�A�̤j�ê��ֽg�Ĥ@�ʽg���۫ߡA�H�s��y�ۤ@���t�֡v�]Campbell
1903: 147�F�Ѿ\Loh 1982: 62-65, 409-412�^�C�H�e���̻~�{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]John Calvin�^��Louis
Bourgeois�]1511�^�s�� <�餺�˸ֽg>�]Genevan Pslter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LD
HUNDRED�A�Y���x�y<�t��>34���u�ѤU�U���U��U���v���ա]Loh 1982: 64-65,
409-410�^�C���ڦ��ɬ±б±q�����t�֤���s�A�o���u�j�ê��ֽg�Ĥ@�ʽg���۫ߡv�O������Peter
Datheen���v�b1566�~�ҥX��<�j�øֽg>�]De Psalmen
Davidis�^�����۪k������ֽg����100�g���۫ߡ]��2�^�A�o���]�OLouis Bourgeois�ҧ@�]��2001�G169-171, 179�^�C
�]��2�^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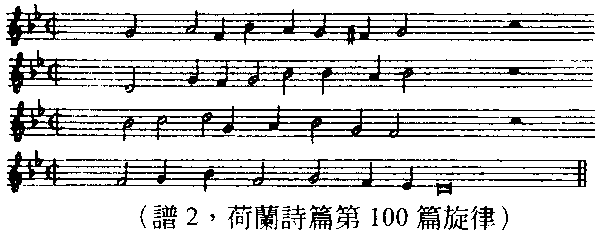
�@�@�ھڥH�W���y�z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űФ@�w�оɷ��ɪ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H�^�H�{�ۤ@�Ǹt�֡A�ұ��̨å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A�u���o�u�Ѥ@�ʭ��v�X�{�h���A�o����F�x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1636�~���k�N��IJ��q�ڬw���Өӥx�����֡��t�֡C�]���ɪ��O�Ƥ����A���_�۬Y���t�֤��ơA�^�H�i�q���Q�C�@���ڬw�k���з|���t�֦�����v�ڡA��x�W²�u���v�T�i��b1662�~�N���W�F�y�I�C
�T�B�x�W�̦������H�ոt��
�@�@Ĭ�������ѱз|�űЮv�����U��v�]James L. Maxwell�^��1865�~����27��]��28��^��x�W�A����16��b�x�n�ݦ�����ΧG�СB��f�]�d1964�G135f�F�}�B�G1965�G7f�^�O�n���DZЪ��}�l�C�_���h���[���j�y���űЮv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v�]George Leslie Mackay�^��1872�~�T��E��b�H���W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DZСC�]�DZлP§�����L�k���}�۸t�֡A�G��N�x�W�з|�ҥΪ��t�֬O�ɥηH������{�Ұ۪�<�i�߯���>�B<����{�ֺq>�B<�X�ǰ�ֺq>��<�ĵ��ֺq>�A��G�̬O�p�ĥΪ��A�ӫe�G�̤j���ݩ���F�|���t�֡C�ھ��v�O��1900�~���e�x�W�n�_�з|���γo�Ǹ֡A�ӥH<�i�߯���>���D�]�d1964�G137�^�C��1854�~��<�i�߯���>�u��13���A1872�~�֦{���خѧ����襻�v��59���]��1988�^�C1900�~�űЮv�̬��M�]William Campbell�^���b�n���s�L<�t�ֺq>�Y�H59����<�i�߯���>���D�A�[�W�@�Ǩ�L�t�֡A�̭����_�x�W���s�@�A���]�L��l��ơA�L�k�d�ҡ]�d1964�G137�^�C
�]�@�^ ���g�Ĥ@���t�֡]1926�^
�@�@1926�~�x�W�j�|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N���X���@��192����<�t��>�A�Où���r�P���u��[�^��]���A�B�`��Tonic
Sol-fa���۪k�A�䤤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A�Y
�Ĥ@���u�W�ҳгy�ѻP�a�v�ե�TAM-SUI�u�H���v�]��<�t��>��62A �^
�]��3�^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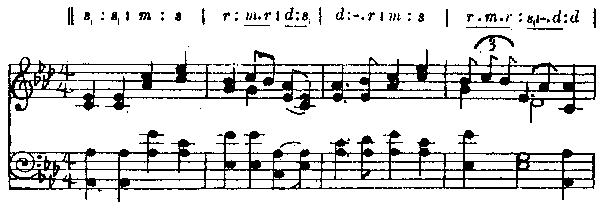
TAM-SUI�u�H���v���D�۫P�{�Τ��۫ߦ��Ǥ��P�C�Ĥ@�Ъ����ĥ|�p�`
| 232 5. 1 1
|�����O�_�Y�Ӧ����쫬�A�b1936�~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F�@�p�`�A�ܦ�
2. 1 5 1|1- - -
||�C���̬۫H232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۫ߴI���˹��ʤ����C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Ӫ��A���ܩ��T�O�H��v�Dz�I IV V�T�өM���Ψ��ܤƬ��D��²��M�n�C
�@�@�H�����űЮvJ. H. Young�g�����D�`�u���ͰʡA�ܤ��ڭ̰��r����A�u���Ĥ��`h?g�a�]��ơ^��1936�~���Q��h?go�n�]�Ƽơ^�C
�ĤG���u�u�D�W�ҳy�Ѧa�v�ե�TOA-SIA�u�j���v�]63���^
�]��4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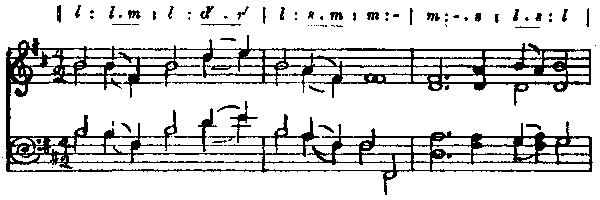
�@�@�u�j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եi��Ӧۥ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u�j���v�C��M�n�O�H��v��
I IV V�����D�A���s�̯�H���۰��}�Y�]6 63 6 12 | 6 53
3 - |�^�βפ�]1. 2 3 21 | 6- - -�^�A�O�s�F���q���¾�ʡA�T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CChauncey
Goodrich�Ҽg�]��Ķ�^�����A�u���ĤT�`�b1964�~���y�Q�ק�A�Y�u�U�˵����`�L�u�A���ȤW�ҬO�ܯ��v�Q�אּ�u�U�˵����l�L�u�A����W�ҬO�ܯ��v�C
��48���u�@�H�ɯɸo�c�h�ݡv�ե�GI-LAN�u�y���v
�]��5�^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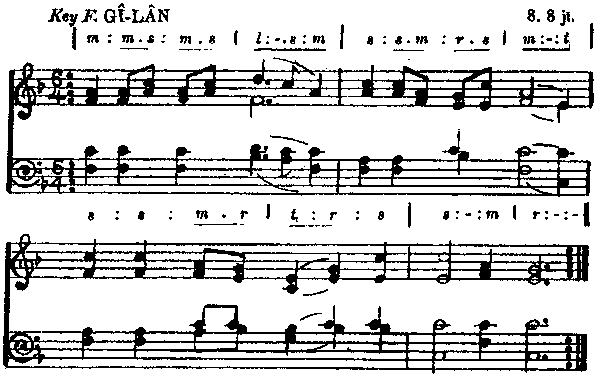
�u�y���v�o�ӱ۫ߥi��Ӧ۩y���a�Ϥ����H�եH �礧�`���A�S�HF�j�ժ��M�n�]I IV V ��V 7�^�B�z�A���۫ߤ��ڥ��S��F�����s�b �@�@�@�@�@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Ϊ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O3 5 6 1 2�A�Y�H6�}�l5�פW�A�G�HF�j�թM�n�꦳�����A �礧�`���]�ܤ��M�`�A��u�ۦp�ݶi�@�B��s�C
�@�@�o�����l�b1936�~�w�Q���N�A1964�~���]198���^���Τ��ꪺ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աu���R�v�A��q���ĤG�`�u�ӧڥ�����c�k���v�w�קאּ�u�ӧڥ�����c�q���v�A�̫�@�`�u�N�n�h���W�Ҫ����v�ܦ��u�N�|�h���W�Ҫ����v�C
��107���u�ɨ�Ѱ�ì��Ҧb�v�ե�TAIWAN�u�x�W�v
�]��6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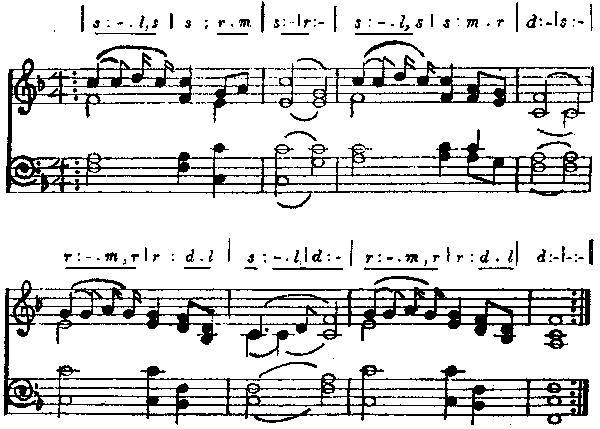
�@�@TAIWAN�o���իܦ��S��Aa a' b b'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C�y���e�T�糣�O�P�˪��ʾ��A�O�@���D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A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ηR�C��q�����Ĥ@�r�u�ɨ�v�令�u�z��v�~�A���\�h�ε����w�令��嶮�β{�N���y�k�C
�@�@�̫�ĤG�y�u���D�C�q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v�]�令�u���D�W�ҭ����t���v�A�b���ǤW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C
��131���u���H�ʩR�L�w�ۡv�ե�BAK-SA�u��]�v
�]��7�^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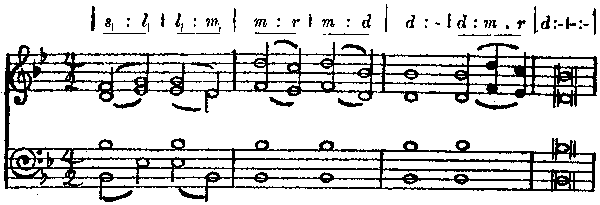
�@�@�x�W�ܤ֦��G�Ӧa�W�s�u��]�v�A�@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@�b�x�_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o�����l�i��O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ڡA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ӷ����ݦҵ��C
�W�ɲ�8���L�q���A�զW��FORMOSA��
�]��8�^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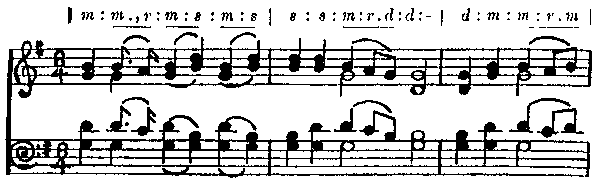
�@�@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A�o��FORMOSA�i���̬���A���L�q���A�u���D���i�t8 8 8 6���֡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´�]�ܧ���]a b c a�^�A�P�ˬO�H��v�DzΩM�nI IV V�C�i���o���]�b���v���Q�^�O�F�C
�@�@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ϧڭ̤F�ѳo�dz��ݩ������Τw�~�ƪ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աC
�@�@�D�`�O�H��ߪ��O�űЮv�̦b�x�űФ��[�N�N�Ѩ������ĥΥ��g�����֯����C���̫�@��FORMOSA�L�q���~�A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Ӧ۷H���q�i�߯��֡r�����Ĥ@�B�T�B�E�B�K�B�|�Q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C�O�ֱĶ����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A�M��@�C�t�W�W�C���q���A�S�H��v��k�ФW�M�n�H���ި�~��p��A�H���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֤�Ʊ`�ѡA�o���O�ȱo�֩w���C�̵��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F�ѡA�۫H�o�Ǽ֦����O�Ъk�@�w²�ƤF�\�h�A��Ӫ��U�ظ˹����B�ƭ����w�Q�ٲ��A�B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O�ݩ@�ڡA���p�H�W�ҭz�A�q�զW�i�����i��P���b�u�H���v�B�u�j���v�B�u�y���v�B�u��]�v���P�a�Ϫ����H�ڦ����C��TAIWAN���P��FORMOSA���G���h�|�L�k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̫ܦ��N���D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h�ﭵ�ֻP�g�֫ܦ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̦b�H���з|�W�D��Ǯɡ]1946-48�^�]�`���Щ����@���ή]�k�]���w���^�C�b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֮ɴN�`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u���X�̡v�@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ӷ��Ҳo�A�����D�Ʀh�A�P���大�D���L���A�G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^�C�G�@���h�åi��u�H���v�B�u�j���v�P�u�y���v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ͦ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̪H�b��z����Ĭ�ѩ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A�L�N���o�{�@�i�����դh���~�]�_�]�����ͼ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H�A�����t��285���u�ڦ��ܦn�B�͡v�Y��κ���v�]Hugh Ritchie�^�@���A�t������
�u�t�ֲ�62A�u�W�ҳгy�ѻP�a�v���Тw���աA�D���ɰ����դh�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s�A���W�K�y�W�R�W�y�H���z�A��63���u�u�D�W�ҳy�Ѧa�v���з��ɥ�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R�W�y�j���z�C�@�K�C�G�~�A�����Ϋn����κ�w���U�X�j���C�ܥi��L�̥Ѥ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Ĥ��v�C
�@�@���N�~������ܤָѶ}�F�����x�W�̪���t�֦��ըӷ����g�C�M�Ӭ_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P<�t��>�W�ҰO���~�N�T���DzV�c���M�C�]1936�~����<�t��>���OTAMSUI�O�u���H��1870�v�I�̽s��`�ѡA�o�O���ӽթ�1870�~�Q�ΨӰt�q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νs�����A�Y1870�~�O���T���A�h�o���դ��O�����դh�ұĶ����A�]�L�O1872�~�~�ӥx���A�G�o���T�إi������k�G�]�@�^�o�Ӧ��լO�n���Y��űЮv�b1870�~�ұĶ��C�]�G�^�_�]�����ͪ����k�Y���T�A�h�i�న���b�Y�~���o�O�H�w�O�Ъ��۫߰t���q���C�]�T�^1870�~�i��O�H���űЮvJ. H. Young�g�����~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~�N�����D�|�ݶi�@�B���ҵ��C�L�צp��ڭ̷P�¥H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űЮv�b�x�űЪ�����Y�w�^�{�F�v�ڥ��g�B�з|���֥��g�ƪ����n�ʡA�ó��w�F��¦�I�ճo�⭺�]�Ψ�L�U���^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ͩұĶ��A�]�L��1901�~�u�@�A�G�o�ǥ��H�ժ��t�֥��w�b1901�~���e�w�b�з|���ϥΡA�ܤ��w�W�L�ʦ~�����v�A�D�`�i�����O�b1936�~�X��342����<�t��>���u�y���v�BFORMOSA�PTAIWAN���½դw�Q�^�O�F�I
�]�G�^1926�~<�t��>���ٿ靈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ǨӤ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աA�Y
�@�@HERALD�G62B�u�W�ҳгy�ѻP�a�v�]1 12 3 32 | 1
1 1 -�^
�@�@AI-CHH�M�]�s�G�^111�u�j�a�۬ݤW�Ҹt�̡v�]6 | 6 - 5 | 5 - 12 |3 - 2 | 2 -�^
�@�@LENG-NA�]�F�x�H�^194�u�ڦ�g���C�q��ʡv�]1 |3 - 3 | 2 1 6 | 1 - 3 | 5 -�^
�@�@KIANGSI�]����H�^210�u�W�ҫߪk�ĥ|�|�v�]56 1 | 653 5 | 65 3 | 21 3�^
�@�@CHIN-CHEW�]�ʦ{�H�^270�u�����W�ҧ��ѳ��v�]55 | 3 2 16 | 1 -�^
�@�@SINIM 340�u�ܮ��U�馳�b���v�]2 3
5 5 | 2 3 1 -�^
�@�@�H�W���զܤ����s�b�骺�q�t�֡r���C�䤤�T��3/4��A�ʥ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~�A��L�U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A�Υi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{�ҳЧ@���C
�]�T�^�x�W���Ĥ@��t�֧@�a
�@�@���ֶ�192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p�@�̻P½Ķ�̤��W�A�G�L�k�T�����_�x�W�H���@�~�A�̷��ɤ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ަb�űЮv�⤤�����p�P�_�A���a�H�i���٥������|�g�s���t�֥B�Q�ĥΦb�t�ֶ������C�ڭ̱q1936�~��<�t��>���~��1926�~��<�t��>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b�x�űЮv�������]
Campbell Moody�^�Ҽg���A�䤭�Ӧ��դ]���O�ڬw�ǨӪ��A�Y
�@�@16�@�U�g���D�q�R�����]RICHMOND���q�t�֡r25�u�q�R�v��אּ�u�ܸt�v�^
�@�@21�@���Y���O�D�@���_�]DENFIELD 45�^
�@�@22�@�ڹ�`�`���|�]BARKWORTH 46�^
�@�@75�@���橼�߱ϥD�C�q�]SOLDAU 217�^
�@�@81�@�D�w��ť�H��ë�]GLAD DAY 266�^
�@�@�o�����t�֤����P���A��ӧ��o�H�O�d�ܤ��C���D1900�~�̬��M�b�n���ҽs���q�t�ֺq�r�w���űЮv�Ұ������A�Τw���W�z�����H�աA�ڭ̴X�i�_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x�W���Ĥ@��t�֧@�a�A�@���@�ӭ^��H��H�x�y�g�X�o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֡A��~�y���y�ڹ�O�H�q�ءC��κ�b1936�~��<�t��>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u�ڦ��ܦn�B�͡v�]285�^���b1926�~���|���X�{�C
�|�B���a�t�ֳЧ@���}�l
�@�@�x�W�з|�b�ϥ�1926�~��<�t��>���~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ťΡA�G��1932�~�ѩ����w���v�]Hugh McMillan�^���D�e�A�d���K���v���ѰO�νs��}�l���s�s��q�t�֡r�A�D�q�饻<�g���q>�B��vI. D. Sanky���qSacred Songs and Solos�r�Ψ�L�ڬ��t�֤���Ķ�ʾl���A��1936�~12��1��X�եΪ�347�����q�t�֡r�A�̧f�u�ͱбª��O�z�A���ɪ��t�֬O�ѲH�����Ǫ����ֱЮv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͡]�L�]�O�x�W�k�n�X�۹Ϊ��Щl�H�έ^�����V�y�����ФH�^�Hþ���˼g�]��^�A�g�G�B�T�~�~�觹���եΪ��]�f1991�G15�^�A���O��Ӱe���饻�L��~���G�D�Ԥ��N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ͩ|�d����襻�A��Ӥ~�i�H�b�x�I�L�C���̤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p342�� 1962�A�ĤQ�T���^�O�ھڥ���G�Q���~�]1937�^�Q�@��27��Ĥ@���A�o�檺�C
�@�@�b��<�t��>�����x�W���a�H�ΫűЮv�̦����ҳЧ@���t�֦p�U�G
�i�����@��
�@�G����G�t�l�C�q��ѭ��{�]91�^�զWLO-SAN�uù�s�v
�@�]��9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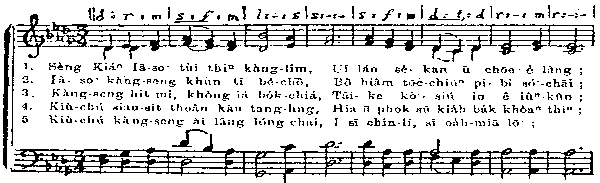
�@�d���K�G�D�D�Хܨ���ë�]261�^�զW�u���O�H�v
�@�]��10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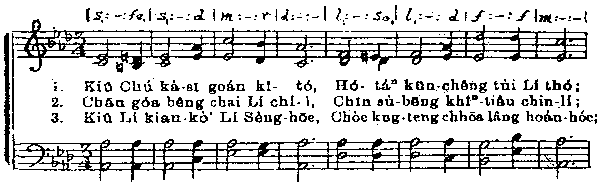
�@�ܸt���Ѥ��A�D�A����ť�]263�^�զW�u�j�ҡv
�@�]��11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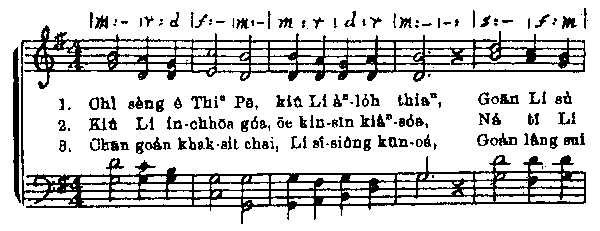
�@Margaret Gauld�]�d�·G���v�Q�^�G
�@�A�Y���ʯu����]317�^�զW�u���s�v
�@�]��12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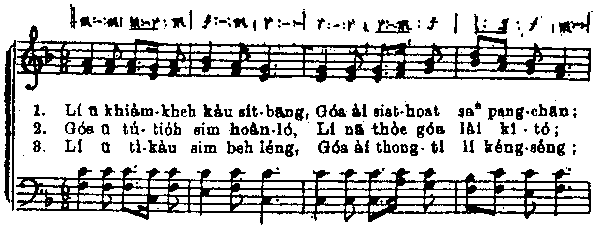
�j�ֵ��@��
�@�����w�]Hugh MacMillan�^�G�W�Ҹt�g�����]184�^
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]186�^
�@�d���K�G�ڪ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ӦV�s�]42�^
�@�@�@�@�@�Ѥ����j�S�O�d�]498�^
�@�@�@�@�@�ܸt�Ѥ����P�§A�]515�^
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]Campbell Moody�^�����]�w�b1926�~�X���A����300���^
�@��κ�]Hugh Ritchie�^
�@�@�@�@�@�ڦ��ܦn�B�͡]285�^
�@��D�a�G�t���W�ү��ѳ��]61�^
�@Ĭ�����G�b���bн���]128�^
�@��ãڡ�G�D�C�M�ئܴL�ܤj�]169�^
�@�@�@�@�@�Ы��j�a�j�n�ۺq�]170�^
�k�@��
�@Margaret Gauld
�PMarjorie Landsborough�]�d���v�Q�A����ͮQ�^
�@GOLAN�u�d���v�]323�^
�@�]��13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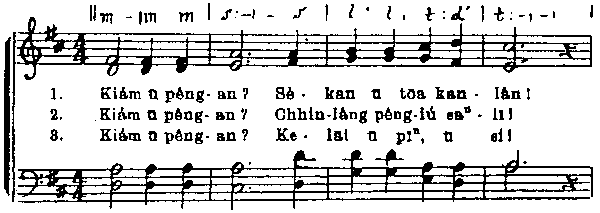
�@�@�b�o�Q��@�̷����űЮv�P���a�H�U���@�b�A�䤤��ݧ@�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P�d���K�A�g�ֵ�����Ĭ�����B��D�a�P��ãڡ�C���Q�|���Ч@���t�֦����x�W�H������G�l�A�Ө䤤�����Ӧ��աA��۫P�M�n���M���O�ҥ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A�|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P�x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o���ϬM�F���ɫűЪ��z���A����{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§ڡ]�x�W��ơ^�Ӭ�W�s��]��v��ơ^�A�Dzߦ��֭��ֺq���믫�ӳЧ@�F�s���x�W�t�֡A�o�ǥx�W�H�̦����Ч@�A�]�O�x�W����{�ܤ��ܳ��w�ۡA�B��H���D�`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t�֡C�ܩ�1926�~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A�u�O�d�F�u�H���v�B�u�j���v�Ρu��]�v�T���A��l�T���i���w�Q�ηR�C
���B�x�W�t�֪��s����
�@�@�G���j�ԫ᪺�@���ܤƫD�`�ֳt�A�x�W�з|�w���{�ūe���y���B�F�v�B�g�١B��Ƶ����D�ԡA����342���t�֤��ܦh�Q�E�@���ڬ��֭��ֺq�O�u�B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ǫ�Q��²��B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ֵL�k�����A�D��1957�~�ۤ�s��s�t�֡C�Ѽw���Q�h�Q�]Isabel Taylor�^����F�ƭt�d�w���A���̦������䯵�ѡA�̫�@�~�ѷ��h�i���v�t�d�q���A���̭t�d���֤��s��A�ש�1964�~�G��A�X���F����523����<�t��>�C
�@�@���ֶ����x�W���s�@�~���ֵ�54���A�s�P1936����19���A�@�p73���A���㥻�t�֤�13.95%�A�s�����զ�15���A�P�¡q�t�֡r��5���X�p20���A��3.82%�C�o�Ǥ�����M�٤p�A���b�x�W�t�֥v�W�w�}�ҤF�s����1�C
�]�@�^�x�W�H���s�@�~�p�U�G
�@�@1�B�ֵ�
���h�i�G�g���٩I�D�C�M�ء]3�^
�D�ڡA�O�֯�i�H�}�]4�^
�ѳ����_�W�Һa���]5�^
�a�P�䤤�ҥR�����]7�^
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|�_ѡ���Y�]8�^
�ߤ��Ŭ��c�H�����]12�^
�D�W�ҵo�X�x�����]15�^
�W�ҬO���k�{�Ҧb�]16�^
�W�����X�ӥl�ѤU�]17�^
���D�Ѥ��űo���ڡ]19�^
�M�ȵ��ԤW�ҡ]20�^
�D�C�M�ءA���w���H�]22�^
�D���U�a�A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]23�^
�Z�Y�ߨx�M�𪺤H�]24�^
�D�C�M�ءA�ѭn���g�]26�^
�~�_�ܰ����K�Ҧb�]28�^
�ܰ����D���R�P�¡]29�^
�W�Ҭ�j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]30�^
�����P�¥D�C�M�ء]31�^
���a�l���V�C�M�ء]32�^
�V�C�M�بӰ۷s�q�]33�^
�ڥD�C�M�ءA�x�W�O�ܸt�]36�^
ѡ�����¥D�C�M�ء]37�^
�W�Ҧ���ڥD�����]38�^
�@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]39�^
�ڤ߷q�R�D�C�M�ء]40�^
ѡ���P�¥D�C�M�ء]41�^
�کҿ˷R�����S�̡]74�^
�W�ұN͢�W�t�l�]118�^
�ڶV�ਭ�L�ӡ]147�^
����Ѥ��O�U�I���]224�^
�ڤ��Uѡ���m�ۤv�]304�^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ꭵ�y�]314�^
�p33���A�䤤32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֡]��224���O�u�w��v�֡^
�d���K�G�D�C�M�جO�ڪ��̡]6�^
�H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ӥh�]43�^
�ڪ��W�ҡA�ڪ��g���]47�^
�D�C�M�ءA�`�y�����]48�^
ѡ����D�X�n�u�֡]49�^
���g���C�M�ء]50�^
�D�C�M�ظt���ߩw�]122�^
�Ѷ}�@���հ��X�{�]138�^
�����b�D�t���]226�^�]�����^
�ߤ��h�a���H���֡]319�^
�ڤߴL�q�ڥD���j�]344�^
�Ѥ����j�a���n�]434�^�]�g���^
�p�Q�G���A�䤤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
���Z�F�G�W�ҽ�֤���U�١]427�^
���D�W�ҬI����֡]433�^
�t�l�C�q���a�W�]450�^
���˦`�G �W�Ҭ����A�R�k���ܡ]119�^�]���q�֡^
�t�{�ݨ��ѳ��y��]153�^�]���q�֡^
�G�A�a�G���ΰ���C�q���ߡ]100�^�]���q�֡^
�����w�G�ڪ��߯��A���ۺq�]69�^
Ĭ�ѩ��G����O���a�x���D�]431�^
�P�ѨӡG����L���ˤH�B�͡]353�^
�@�@2�B����
�d���K�GKAHOVOTSAN�]434�^
�]��14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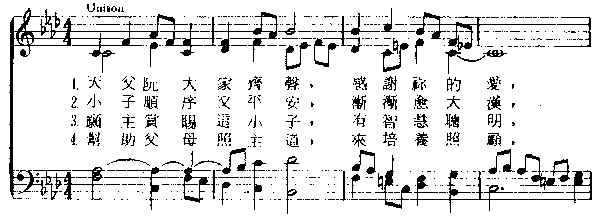
���r�v�G��@ TE DEUM LAUDAMUS�]517�^
�]��15�^

NUNC DIMITTIS�]518�^
�]��16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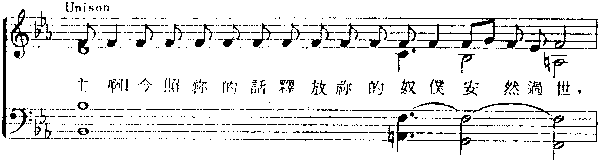
�s�@ B�K-SA�u��]�v�]233�^
�]��17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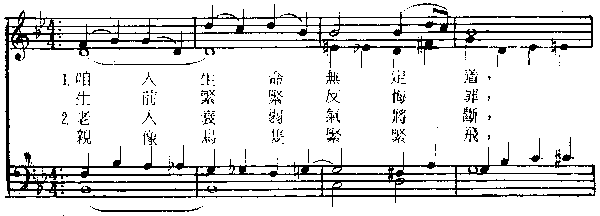
T�A-L?N�U�u�j�ѮQ�v�]443�^
�]��18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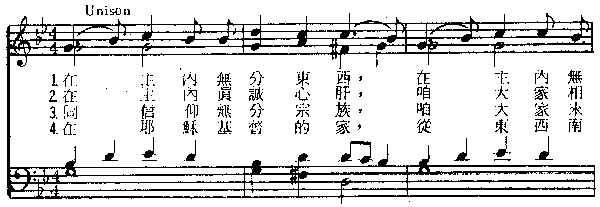
�d���D�G��@PATUNAKAI�u�űЪ̡v�]226�^
�]��19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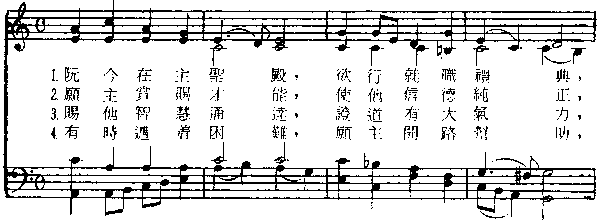
HU-SIAn�u�����v�]427�^
�]��20�^

L?KANG�u�Ҥu�v�]450A�^
�]��21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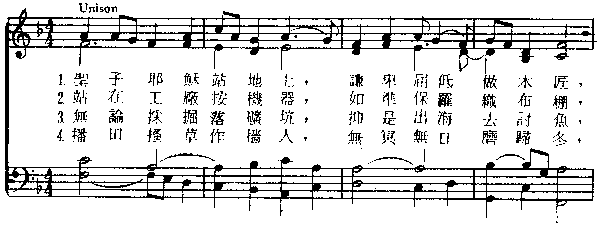
�s�@TAMSUI�u�H���v�]62A�^
�]��22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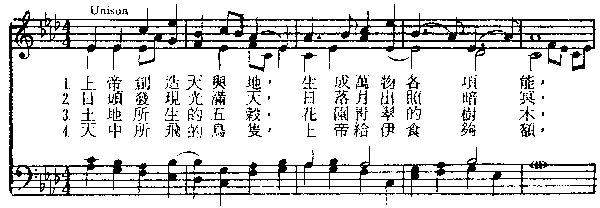
T�A-S�A�u�j���v�]63�^
�]��23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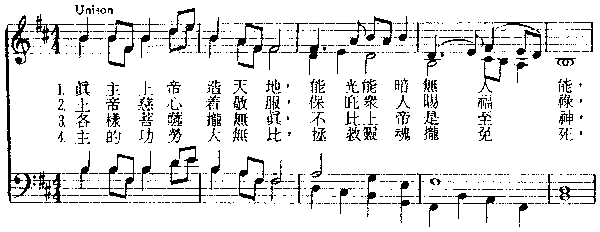
QUEM PASTORES�]88�^�]�w�ꦱ�ա^
S�NG-CHHUN�u�ӬK�v�]97�^
�]��24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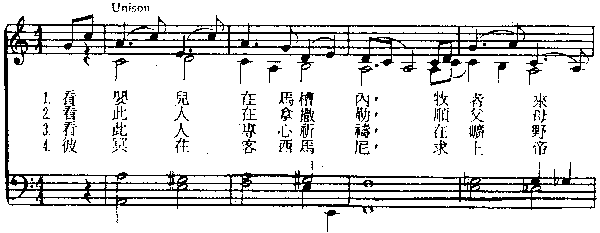
L?H?TH�M�u�U����v�]199A�^
�]��25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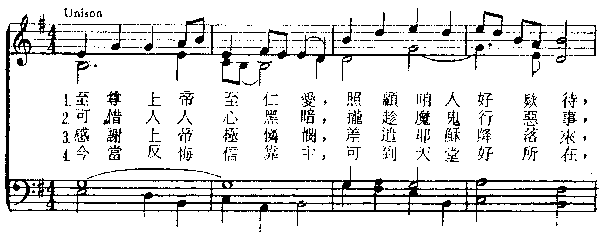
KIANG-SI�u����v�]210�^
�]��26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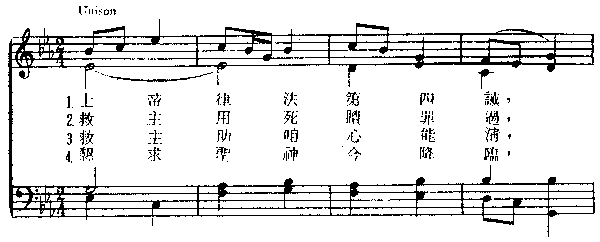
KAHOVOTSAN�u�ͤ�v�]434�^
�]��27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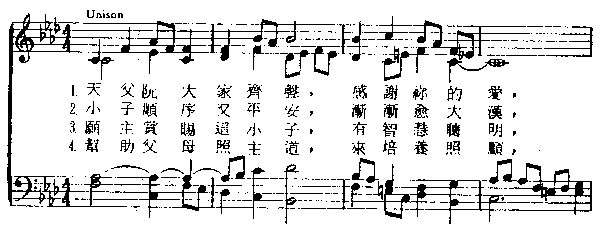
��L�٦��Ӧۤ��ꪺ���աG
�@�@AI-CHH�M�u�s�G�v�]111�^�BP?P�E�u�_���v�]167�^�BL�NG-N�u�F�x�v�]194�^�BP'
U-TO�u�����v�]244�^�BCHINCHEW�]270�^�BTI�U�u�l�v�]329�^�BSINIM�]340�^�BCECILIA�]395�^
�Τ���@�̡G�J�P���w�]SAVIOUR'S LOVE 191�BCHIA HSIANG�u�a�m�v 237�^�A
�@�@�����s�]HOLY
LOVE�u�t�R�v198�^�A�Ŭ���]�űЮv�^ �]THE BROOK CHERITH 254B�^
�]�G�^���ֶ����S�I
�@�@�iù���r�P�~�r�åΡA�B�N�~�r�ӤJ�Ф�����۹|�C
�@�@�j�R���¸t�֤��\�h���ǤW�έ��֤W�����z�Q���֭��ֺq�A��l�O�d�b�t�֤���b���A�ϥx�W�з|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O�u����n�H���C
�@�@�k�W�s�F�t�־Ǫ������A�ĥγ\�h�j�N�B�Q�K�@���H�e�β{�N���P�ɴ��t�ֵ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@�~�A�G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ǻP���֪��~��P�{�סA�p:
435 �u�C�~���n���̡v, ascribed to Clement of Alexandria (150?- 220?)
242
�u�D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ڡv, Synesius of Cyrene (375-430)
376 �u�ܸt�Ѥ��A�w�ߪ����v, Greek, 4th C.
320 �u�W�ҬO���w���n��v, Martin Luther(1483-1546)
73 �u�����P�¤W�ҡv, Martin Rinkart
(1586-1649)
115 �u�ڤߥ���Q�r�_�[�v, Isaac Watts (1674-1748)
246 �u�W�ҷR�h�ӹL�@���v,
Charles Wesley (1707-1788)
�@�@�l���U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ΡC�]���U��(�|)�^
�@�@�m�����s�J�D�`���㪺���B���@�̨ӷ��B��ߡB���W�B�^��B�~�r�B�ոܦr������θt�g���`���K�ӯ��ޡA�H��K��֤θt�־Ǥ���s�C
�]�T�^ �s�t�ֱ��Ҥƺq�������{�G
�@�@�P1936�~����<�t��>�ۤ�A1964�~����<�t��>��q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嶮�A�B�~�r�Ϊk�����j��A�L�h���թηH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pko�in- ko�in�A�w�令���x�y��ko -kon�C���\�h�λy���P�x�W��Ʈ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|�ƨҦp�U�G
�@�@���h�i���v���u����v�Ρu�m��v�g���t��224���D�`�A�X���a�ۭ���§���A��λy�u�k���ѥ��P�߷q���v�B�u���y�İ_�@�D�H�ߡv�A314���u�Y�L���R�N�ܪŪšA�˹����r�Ұ��v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a�H���f���C
�@�@�d���K���v�Ҽg319���u�ߤ��h�a���H���֡A�����Ѱ�I�Q�v�A�̫�G�r�O�D�`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{�k�A434�����p�İ��u�g���v�]t?ch�^�Ρu����v�O�x�W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j�ơA��λy�u�{�M�p�Ѩϡv�B�u���з|�ɼ١v���ݥx�W�����{�N���λy�C
�@�@���Z�F���v���t�֥i���O�̴I�x�W�S�⪺�@�~�A���ެO�֪��ε��B�����B�`���B���e���ݤW�����ǧ@�A�p433���u�O�j�O�p�H�D����v�B�u���O�l���A�ҩd�O�ѡv�B�u�ݤH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v�B�u�w���u�v�A�q�@�����v�F450�����u�L�ױı����q�|�A���O�X���h�Q���v�A�u���зk��@¨�H�A�L�ߵL��i�k�V�A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p�ï]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ͰʡA�B�P���ɥx�W�H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427���u�W�ҽ�֤���U�١v�]��אּ�u�x�W�U�ҡv�^�y�y���O�x�W��ƺ��誺���{�A��x�W�H�����v�[�A��G�m�j�۵M���R�n�P���ݡB��a�x���|���M���B�ĦX�B��F�v�����q�Υ@�ɤ��M�����@�F�H���W��²�n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A�D�D��֡A�i���O���ֶ����̨Τ��N���@�A���C���֥H�ѪY��C
427���]�u����U�١v�אּ�u�x�W�U�ҡv�^
�]��28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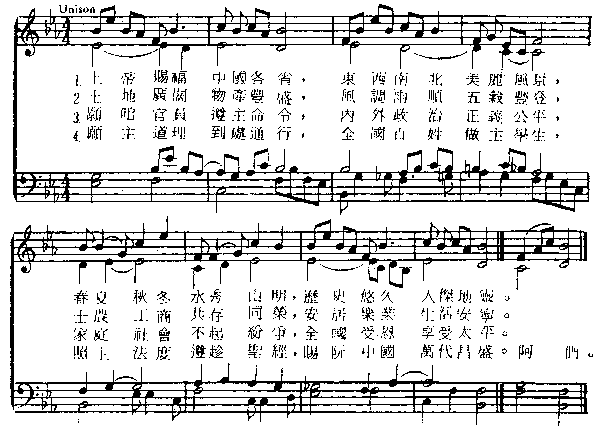
�]�|�^ �s�t�֦��ձ��Ҥƪ����{
�@�@�b�@�@15���x�W�H�ҧ@�νs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F�@���]88 QUEM PASTORES�^�O���w��t�ַs�t���M�n�A�٦�210 (KIANGSI)�O�Ӧۤ��ꪺ�۫ߥ~�A��l���۫߳��i�{�@�p���x�W����A�䤤��62A (TAMSUI)�P63 (TOA-SIA)�O�q1926�~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է�t�s���M�n�C�Ħۭ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233�u��]�v�]<�t��>���~�٤���աA���אּ���H�ա^�A443�u�j�ѮQ�v�]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ա^�A97�u�ӬK�v�A199A�u�U����v�A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K���v�ұĶ����C517�u�g���|�v�P518�u�譱�|�v�O���r�v�ժ��ۥx�W�~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֤��ʾ��ҽs���u�w���C434 KAHOVOTSAN�]�ͤ�^�����լO�����饭�H�����Ч@�A�ѵ��̩M�n�A226 PATUNAKAI�]�űЪ̡^��450A�u�Ҥu�v���O���̨̺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ҳЧ@���C427�u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ʾ��h�Ħ۸k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p���v�C
�H�W�o�Ǧ��ժ����椤���T�ӯS��G
�@�@�i�۫ߧ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H�^�κ~�H�H�L�b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S�ʡC
�@�@�j���r�v�ժ����M�n�ĥ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i��]�p233�^�A���ܤƩM���]517�B518�^�C
�@�@�k���̥�ҥ鳯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]97�^�A���ߥμҥ魵���P���۫ߡ]427�B434�^�A���٥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DzΤQ�K�B�E�@���@��ɴ�������]Common
Practice Period�^�A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զ��M�n�]62A, 63, 199A, 210�^�C
�@�@²�����A�q���֥߳��[���A�x�W�~�H�ҳЧ@�s�t�֪��۫ߤw���ҤƦa�]contextualized�^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H�^�κ~�H������A�u�O�b�M�n���B�z�ޥ��W�|���d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νզ��]modal�^���@�ġ]Syncretistic�^����A�|����}�B�o�i�X�@�M�A�X��x�W�կ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
���B�x�W��L�ڸs�y�����t��
�@�@�H�W�Q�ת��O�H�H�f��70%���֨иܬ��D���t�֤��R�A��L�|���Ȯa�H�]����14%�^�έ�����]��2%�^���t�֡A��²���p�U�G
�]�@�^�Ȯa�t�֪����{�O
�@�@�x�W�b�Ȯa�m�����ű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w�A�B���x���A���G�~�e�]1999�^�Ȼy�t�֪��X���o�b�x�W�з|���֥v�W��ߤF�@�Ө��{�O�C�ڭ̭n���ߨ�D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һ�ɤU���t�ֽs��e���̡A�L�̪�F�C�~���ߦ�j���B½Ķ�A�s��F�o���t�֡A�b350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71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աA�䤤30���O�s�Ч@�A25���Ӧ۫Ȯa�Υ��g�����A�٦�16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Φ��թηs�@�]���m�Ȯa�t�֡n�ǡ^�C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Ȯa����{��ۤv��ƪ��֩w�A�]���{�L�̶}��B�]�e��L�ڸs�����֤�ƪ��믫�A�`�H��L�̤��᪺�űФΰ���{�ޮa�P�ϩR���V�m�|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^�m�C�H�U���|�ƨһ����C
�@�@�u�W�үk���@���H�v�]109�^�O�h�~�h�����S�òK���v�]�H�q�|�^�Ҷ��A�L��x�W�~�ڤ��֨лP�Ȯa�q�ΥB�̬y�檺���q�u����աv�A�ΦW�u���v�A�Ρu�s���k���˸U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Y���v�D�`�y�[�A�q����Ǩӥx�W�A�a����B���M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۫ߡA�H�D�`�Ȯa�Ƥ��y�k�����t�g���̭��n���g�`�]�����֭��T���Q���`�^�꦳�S�O���N�q�]����29�^�C���M�O�M�ۡA���۫H���o�ӭ��֤�ƪ��Ȯa���H�|�ܦ۵M�a�_�G�J�B���J�Χj�_�äl�@����B���ƭ��ĪG���C
�]��29�^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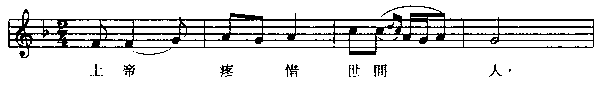
�@�@ �u�q���W�Ҧ����z�v�]153�^�O���ؤ��̫Ȯ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Ф��t�֡A�L�H���ۡ]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ƭ����ĪG�A�����J��v�M�n���U�M�A�O�@���\����d�C
�]��30�^ 
�@�@�u�t�l�C�q�ӭ��{�v�]247�^�O�^�w�F���ѥH�u�K��Q���߬v�v�v������W�dz��t�l�C�q�X�ͪ��έ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߮�v�v�����ֻP���Q���Ȥ��g���n�c���@�T�u�����t�ϵe�A�O���i�h�o���u�}�@�~�C
�]��31�^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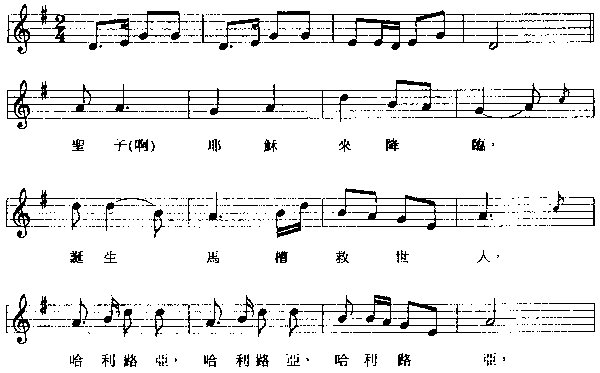
�@�@�o�DZĦۥ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է��O�d�즳���e���ζ����A�G�O�s�F�ӭ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ʡA�B���t�H��v�M�n�A�o�O�L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֪��̨Ϊ��{�C
�]�G�^������״I���t�ָ귽
�@�@�x�W�b��v�ɥN�w���~�H�ΫűЮv�έ�����]�p�ۭb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űЪ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űФαШ|�l��1946�~�E��Q����A���ɷźa�K���v���]���U���v���e�U�e���Ὤ�I�@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]�v�}��t�ѾǮաA����ǹD�H�C�@�E�|�C�~�h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s�b�F�����A�ګűСC�P�~�d���K���v��x�F�a�Ϧb�����ڡB���n�ڡB���W�ڡB�|�ͱڤ��}�ݶǹD�A��@�E���@�~����Q�T��]�춮���ڡ]�F�^�^�]�з|�]�}�B�G1965�G369f,
398�^�C�n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k�h�P�\���~���v�ۤ@�E�|���~�}�l�b���W�ڤ��ǹD�]�}�B�G1965�G427-429�F�_1992�G1-6�^�C�ƤQ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з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٬��O�u20�@���űЪ����ݡv�C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éʵ��}�A�r�}�֭��~�A�з|�t�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P�L�̳߷R�B����q�۪������з|���űлP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U�q�C�b�@���᪺���ѡA�L�̦U�ڧ��w���䥻�ڸt�ֶ����X���C���̦����Q�@���ֶ����̦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K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֡]�@�E���K�~�^�A�䤤�w���ĥΪ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Ƭ��t�֪��]�p150��Surinai
a pituulan���^�C
�]��32�^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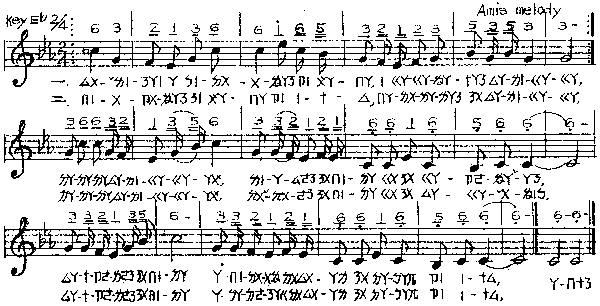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�|��~�Ӥ��ƨҥH�e�ܭ�����t�ֳЧ@����p�C
�i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@�q������|�ֺq���r�]Sapahmek to
Tapag�A1992�^�O�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ڤ��t�ֶ��A�@��200���A�䤤�̫e���|�Q�����O�Ħۥ��کΥL�ڤ��DzΥ��q�A�θg��s���ηs�Ч@���t�֡C�����R�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
Kalimlaan a Limo'ot���O�̶DzΤT�|���X��²�Ʀ����G�n���t�֡A�ĤG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Ұ۪�Ħ����۫ߡC
�]��33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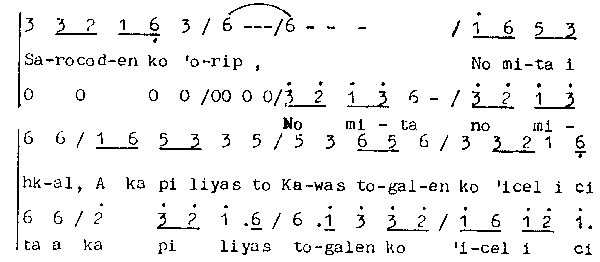
�@�@�t�@���O���̱��ж�ֽg136�g�����A�L�M�窪�v½Ķ����O Sapikansya a
Radiw���]#4�^�C�o�O�嫬�������۪k�A�|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T���X�ۡA�D�۫ߤ��~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ܡA����̫�ƭ����פ�h�k�^���ۡC
�]��34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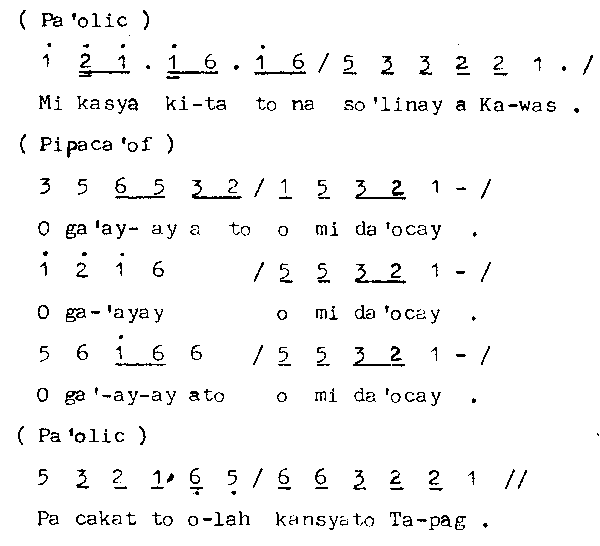
�j���A�t��
�@�@���䤧�Ĥ@�����A�t�֬O1975�~�E��Q����ѥ��A�t�֩e���|�X�����A�@�@��375���A�O���A�y�P�x�y�]�~�r�A�Τֳ����O�_�ʻy�^����ӡA�ϥ�²�СC�䤤��12���O�Ħۥ��A�Dzα۫ߡ]112,
156, 158, 162, 168, 187, 188, 195, 211, 215, 244,
277�^�A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ա]51�^�Τ@���y�榱�����۫ߡ]57�^�A��L�٦��ƭ��O�x�W���H�ա]166�^�A����]330,
327�^�Τ饻�]190�^���C�B��²�Ъ����ޡA�e���d�ߡC
�@�@���A���X�ۤj���Hdo-mi-sol���D�b���X�ۡA�q�G���줭�B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P�`���]homophonic�^�M�n�A����۵M�x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O��L���ڪ����֩ҨS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M�t�֤����Хu�O�D�۫ߡA���|���|�ܦ۵M�a�t�W�M�n�A��M�n�����Ǧ]�H�Ӳ����۪k�A����DzΪ��зǰ۪k�̵��̪���s�]Loh 1982: 326-330�^�̫ᤧ�פ����do-sol���M�n�A�S���T��mi�A�զ��A�h�O��~�өҥ[���C
�@�@1984�~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t�֤@�@��360���A�䤤���A�Dzα۫ߦ@�p23���C
# 271"Kuda Kauna
Makanmihdi"�]��ڳo�̨ӥH�o�w���^�O�j�a�ܳ߷R���@���֡C
�]��35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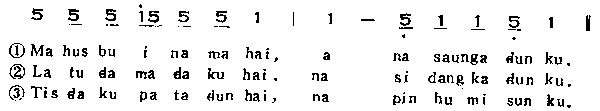
�@�@�t�~�@��269��Paiska lau
Paku���]�q�{�b�}�l�V�O�V�e�^�A�ѷ|���^��U-I-Hi���۪k�A���w�Ǩ��~���@�з|���E�|���C�]�\�ڭ̥i�հ۰۬ݡC
�]��36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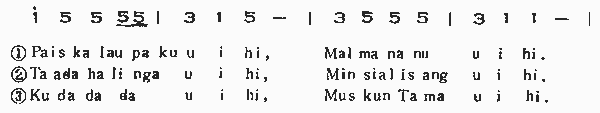
�k���W�t��
�@�@���W�ڤ��Ĥ@���u�t�֡vSenai tua Cemas�O�űЮv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]John
Whitehorn�^���D�s�A��1967�~�X�����A�p208���A�H�`���Ÿ��t�u�v��²�С]�|���^�]�L�A�䤤�C������O�νզW���O�X�A�B�t���\�h�ڬ����n���t�֡A�p�w�ꪺWATCHET
AUF�]48�^�A�^�ꪺDIADEM�]52�^�A�k�ꪺ�t�Ϲ|�qIRIS�]18�^�A�o�Ǹַ��ɳ��٥��X�{��x�y���t�֡A�i���|���ĥα��W�աA�L�̥u�ĥΤ@�����H�u�j���v�]9�^�A�٦��@�����y�榱�����q�]195�^�A��L�T���饻���t�֡]43
WAGAKO, 183 HAHANO MISUGATA, �P192 AKATSUKI�^�C
�@�@�̪�@���q���W�t�֡r�]Senai tua
Cemas�^��1996�~�X���A410������80���]331-410�^�O�ѱ��W�ΥL�ڪ��Dzα۫ߧ�s�ηs�Ч@���t�֡A���Ƿs�@�w���DzΪ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䤤���F�O���ںq�S�⪺�t�֡C
�@�@370 tau cike liyamapulat�O��۫ߤ��q���C
�]��37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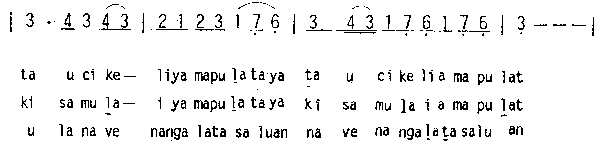
�@�@350 mali mali�h���j�դG�n�����X�ۡA��ĤG�n���O�Ѩk�n������{�C���]reiterated
drone�^�A�t�ۮɳ̫�פ�n���O�a�ۤU�ƭ��]breathy terminal glide�^�~����F�䭷��C
�]��38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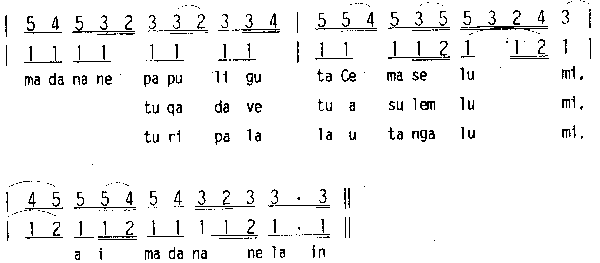
�l�Ӿ|�ոt��
�@�@1994�~�X�����q�Ӿ|�ոt�֡r�]Suyang
Uyas�^�p��330���A�䤤���ڪ��t�֭p��36���]295-330�^�O�Ħ۶Dzα۫ߩΨ̶Dzέ���Ч@���t�֡A�o�DZ��Фηs�@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O���K�a���v�]Hayu
Yudaw�^�C���ֶ����u�I�O�j�P�O�s�FTruku²��|�n�����]re mi sol la�^���쫬�C�p302 Taga Han�]�е��ݡ^
�]��39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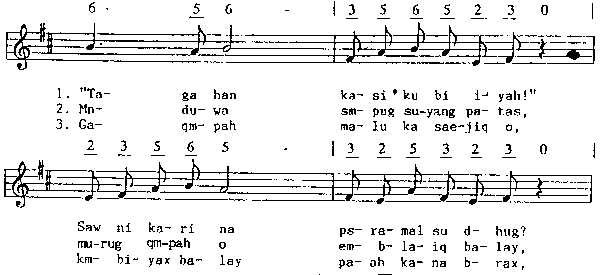
�C�B�x�W�t�ֳЧ@�{�p�G
�@�@���F�W�`�Ҥ��ЫȮa�P������t�֦��դ��j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ĥζDzΪ����q�~�A����x�W�з|�q�Ƹt�ֵ����Ч@���ä��ܦh�C���̳Ч@���椧�t�O²���p�U�G
�]�@�^ �H��v�DzΩM�n���D���@�~�G
�@�@���ѱз|���Ʀ�۷����D�B�h�����t�֧@���a�p�����M�б»P�������Ѯv���A�L�̤G�쳣�O�H�Ч@�֯Z���X�ۦ����D�C���б¨åB���\�h���T�֦��B���B�W�ۦ����@�~�C�L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j��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۫ߤj�������籡�B�u���B��ť�A�����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M�n���B�z���i�{���q�j��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ޥ��C�S�]�L�O�@��X�⪺���^�t���a�A��q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A�B�ߥμw��W���M���A��C�M���A�Τj�p�ղV�X�M���]��1996�G92-99�r�C���M�L���@�~���ݦX�ۼ֡A�����ǥ�i�@���|���t�֡A�p�u�C�q�l�ڨӦ�Ѹ��v�]��40�^�B�u�Dë��v���C
�]��40�^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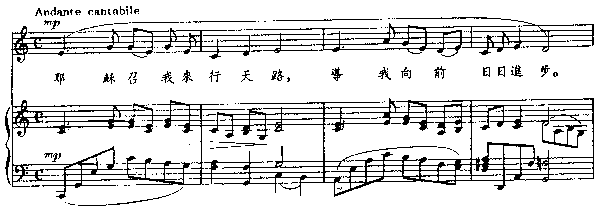
�@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Ѯv�w�X���F�ܦh���T�|�ʭ����X�ۦ��B�ൣ�X�ۤΫe�����C�L���@�~�X�G���O�H��v���թʩM�n����¦�A�L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ĥΥ����۫ߡ]��1996�G54�^�A���L�`�]���w�εL�b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{���a�۫ߪ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Ǹ�²�檺���l�A��i�వ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t�֡C
�]��41�^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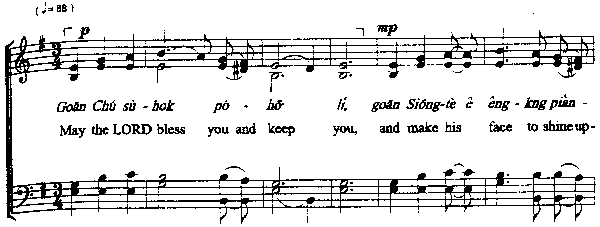
�@�@�t�~�A�D�`���۩�x�y��Ǥ��Ч@���C�H�P���v�]�@�F���֦��l�C�\�ѽ媪�v�Ҽg���u��m�v�]���F�ұ�Ѷm�^�ѥL�Ц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ѩM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٨Χ@�C
�]��42�^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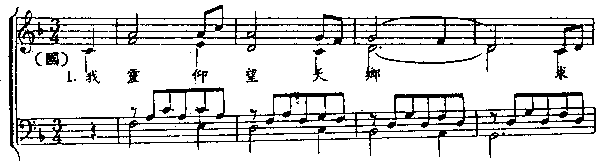
���ѱз|1985�~�X�����s�t�֡]���^�@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|���O���a�H���Ч@�A�䤤�G���ѧ����檪�v�@�����A�u�Ȧ谨����餺���v�]25�^�]��43�^�Ρu���D�Ѥ��P�����v�]37�^�A�⭺�q�����ƨΡA�۫߫h���H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A�I���x�W���A�M�n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A���]��37���O�űЮv�w§��]Raymond
Adams�^���M�n�^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Dz���H�C
�]��43�^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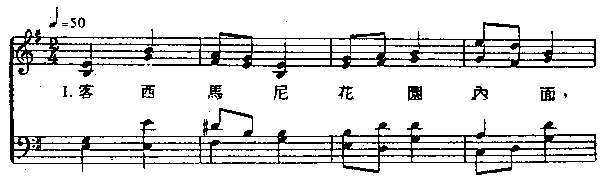
�]�G�^���y��֭����C�~�s�@
�@�@�����q�n���@�̸s�ҥX�����t�֦b20�h�~�e�N�}�F�x�W�y�歷�t�֤����A�䤤�H�d��ɥ��ͩҳЧ@���u���a����v�̬��z���H�f�C�L�̦b�q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t�۷��ޤH�A���إ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ֺq��~���H���ܤj���v�T�O�C
�]��44�^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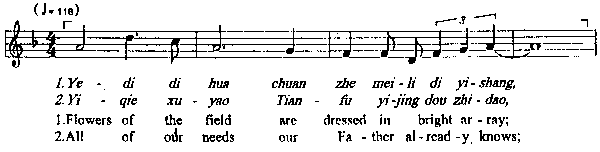
�@�@��~�ӥt�@���O����O�H����[�{���m�F���j���窺�u�g�����u�v�@�̸s�A�X���F�\�h�s�q�A��h�H�y��֭��A�����۫ߨ̺֨иܪ������ӵo�i�A�O�H�ԮԤW�f�A�S�[�H�y��u�q���g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v�M�n�B�N�L�M���B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Ѥְg�K���дo�A�˼˳��O�W�ҹw�ƪ����h���A�p�u�C�M�د��ֺ����v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{�a�a���ҳ߷R���y��t�֡C
�]��45�^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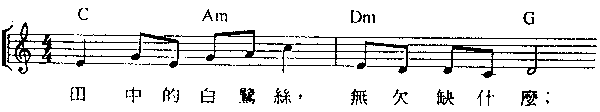
�@�@�t�b�u���K�ֺq�v�ĤG�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O�N�b�@�����k�H�e���x�W�y��q��s���Ӧ����t�֪��A�p�H�B�媺�u��K���v�ܦ��u�j�a�o��S�P�ߡv�A�i���F�Q���u�N��v�ܦ��u�۷R�k�v�A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u�䳣�]�B�v�ܦ��u���髥�������ë�v�A�o�dz��O���쪺�C�H���X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ּƤH���w�ۡA��}�D�ͥi��]���ǧl�ޤO�A���ڭ̥����Ҽ{�q�y��q�n�ܦ��t�֤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P���μ@�����p�Q���~�A�@��H��y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A�סA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P�~��Ψ�\�Ρ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Ǥήɶ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C
�@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h�q�쬰�u�L�N���v�A�b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p�S�i�Y����s���A�G�令�t�ֹ�ڤH�õL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A�u�n�p�߳B�z�`�H�|�����פ����G�C�ܩ�@�Ǻ~�H���v�y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H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]�w���\�h���P���q���A�t�۪��H���H�a�i�Y������A�G��H����ЫH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]�O�ܦ۵M���{�H�A���̦n�]���g�L�Ч@��s���@�ؤί��Ǫ������~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C
�]�T�^���̴M�ڳЧ@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@���̦~���ɥѼҥ���֭��ֺq������}�l�Ч@�t�֡A�g�L�H�㦳�~�H���椧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۫߰t�H��v�DzΩM�n�A����զ��M�n�A�̫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M�n����z�A�H�ƭ���줧�ޥ��i�{�F��۫߬����z�Q�C1970�~�N�X���G��ɪ��v���u�@���a�Q�v�]�q�s�t��I�r48�^��Fred
Kaan���u�W�Ҧ��t�H���z�v�]53�^�A��M�n�O�B�Υ���|�פι��۫ߡA�^��з|���ֵ��aErik
Routley�����סu�@���a�Q�v�H�L�b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p�T�n����Invention�]�ګ��зN���^�]Routley
1981:183�^�C�ܾl�~�ӵ��̬��l�M�Ȭw���֯S��Ӵ��ҥ�Ȭw�U���ڶDzέ��֪�����@�F�h���t�֡A�p������Ȭw����Ш�|���t��<Sound the
Bamboo: CAA Hymnal 2000>�����u�W�D�����ѳ����ˡv�]The God of Us
All�A181�A�饻���^�A�u�C�q����o�ۥѡv�]Jesus Christ Sets Free to Serve�A247�A���ꭷ�^�A�u�֩M����v(Hunger
Carol�A144�A�L�����^�A�u�R�h�t���v�]Loving
Spirit�A220�A�L���^���A�B�U�t�W�P�Ӭ�����Ƭۦ��Φۤv�y���M�n�]�Ԩ��d2000�G398-427�^�A�i���]�b�x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ֵ��A�o�Ǹ֤j���O�~��H���@�~�A���̥H�^�y�Ц���A½���x�y�A�b�q�o�ǥ��ڭ��֤���o�ҵo����A���̭���ۤv�x�W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֤�ƨӴM�ڻP�F�P�C�q���u�V�C�M�ذ۷s�q�]�|�^-
�q���K��a�y���v�]�d2001�G1-19�^�̵��̦C�|�K���x�W���ڭ��֤�����ҳЧ@���t�֡G�K���H�u��Q�_�v�Ψ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ʾ��]��46
�u�W�ҽ�֥x�W�U�ҡv�^�B�|���H�Ȯa�����]��47�u�H�ͱ`���٬ޤ����v�^�B�T���H�n�ީΥx�W�־��]��48�u�W�D���R�v�^�B�Q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Ф��t�֡]��49���A�u���R��³�v�^�A�w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v�DzΩM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ӥH���ƭ��ĪG�έ�����U�گS�����h�n���۪k�A�b�b�ҥH�ҴM�o�x�W�U���ڭ��֤�Ƥ��ڬ���¦�B�[�c���Ц��s���C�o�ǴM�ڪ��Ч@���b���ն��q�A�٥������A�|�ݧ�i�A�q�нѦ���i���[���СC
�]��46�^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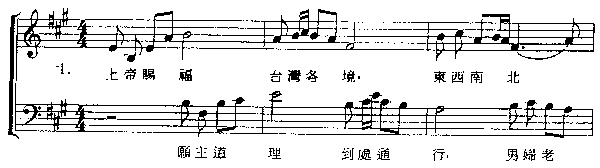
�]��47�^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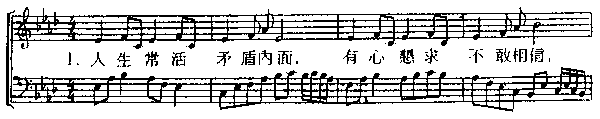
�]��48�^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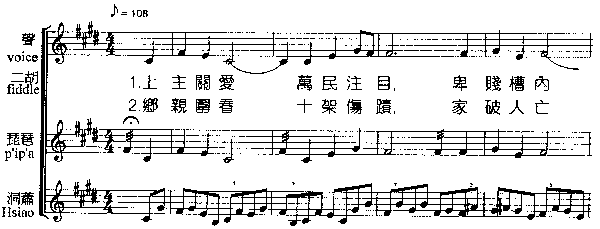
�]��49�^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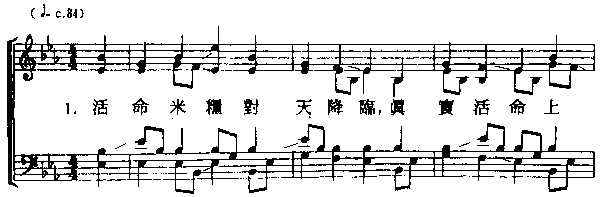
���סG
�@�@ ��X�H�W���M�ڡA�ڭ̥i���H�U�����סG
�]�@�^ �H���Ǫ̬۫H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C�d�ػy���P��ơA�C�Ӥ�ƥ糣�㦳��W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A�H�o�ǯS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{��믫�ζǹF���Q�B�P���B�ΫŴ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v�ЫH���O�L�̻P�ͭѨӪ��v�Q�A��@�~����L�i�_�w�B�L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C
�]�G�^ �x�W��Ӫ��|�P�з|�]������Ƥ��v�T�L���Y���A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F���H��褧�f���[�P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̾ڡA�P�Ϥj�h�ƪ��ʩm���h�F�ۤv��ƪ��ڡA�ר䭵�֤H�u��Y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v�j��β{�N�y�歵�֡A�з|�P�ǮձШ|�Ұ��i�X�Ӥ��R�v�߲z�A�ϥL�̫����{�P�δL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֤�ơC��~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ﵽ���{�H�A�����j�h�ƪ��з|���ֳЧ@�̡B�Y��̻P�|�����ɦV��κ������v�μҥ��v���t�֧@�~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ڡC
�]�T�^ ���ڭ̥x�W���F���P�з|���n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b��ڤW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ڡA���F�v�B�g�١B��ޡB�dzN�ί��Ǥ��~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ƥ������W�S���^�m�C���F���ؼСA���̻{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G
�@�@�i�x�W���@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δ��@�P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A���A�F�a���ɡB��q��v�β{�N���@���ޥ��]�p�饻���Ӭ۾��u�~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~�@�ˡA�@�o��ڬ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^�A���Ч@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P�H���{�N���ֻP�{�N�з|���֡C
�@�@�j�{�P�B�L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ڤ����֤�ơA�����B�M��B��s�ڭ̥x�W���֪��ڡB���֪��F��A�Ч@��i�{�x�W�U�ڸs�S������P�M�n���@�~�A������@�ɤδ��@���з|�b�x�W�����ֻP�з|���ָ̤��ɨ�P��L���ڭ~���B�x�W�H�W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