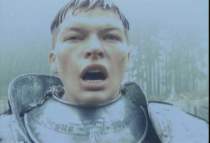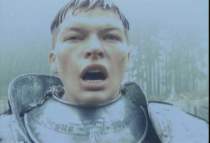● 第三個關鍵性的形式對應
我們把這部電影兩個對應形式,與黑衣人三次跟聖女貞德的對話重點,畫成對稱形式如下:
| 與上帝合一 | 上帝給我使命 | 聽不見聲音 | 上帝豈真的需要妳? |
| 聖杯的血酒 | 來自天上的劍
(神蹟) | 不要等奇蹟 | 妳選擇自己想要看的 |
| 十字架 | 旗幟 | 劍 | 只為「師出有名」 |
處理完這個形式對比,我們差不多要接近整部電影最核心的主旨了。
根據基督信仰(廣義的定義,包含天主教),撒旦也曾試探耶穌,三次跟耶穌有重要的談話。撒旦談話重點是放在要耶穌行神蹟自解困境;承諾給世間所有權勢,只要膜拜撒旦;以及誘使耶穌試探上帝,以疏隔耶穌與上帝的關係。這三個試探,都是撒旦企圖讓耶穌放棄祂最重要的使命:步上十字架的世界拯救之路。
但是耶穌嚴厲拒絕了。神蹟、權勢、質疑上帝試探上帝,都是容易走的路。
而不信耶穌的百姓,要求耶穌行神蹟以驗明正身,耶穌也還是答以除了上十字架的使命,沒有其他的神蹟。
基督教信仰中的神蹟與使命往往蘊含一個很難讓人徹底瞭解的觀念:那就是在基督信仰中,真正重大的使命,往往都需要透過「死亡」之路而得:「一粒麥子死了,便生出許多子粒來。」十字架之路就是使命之路,它讓人看見的永遠不是榮美權能,而是死亡,是在死亡後後爆發的新生,看到真正的神蹟。
耶穌是死後的復活,方使救世福音傳往地極。
根據歷史,貞德承受火刑才是法國轉敗為勝真正的關鍵,因為自此以後,法國人民群起激憤,再也不依賴「洛林處女預言」的,靠四面八方各處農民的團結一致,終於使英軍不敵,退到海峽那一端去。
● 盧貝松「聖女貞德」探討的焦點
而盧貝松聖女貞德這部電影的形式與敘事,我們到此已經可以斷定,盧貝松並不像德萊葉的聖女貞德,將焦點放在貞德的「聖」與「受難」上,他其實是透過這個故事在歷史中若干重大的懸疑間隙,嚴謹而細膩的把焦點放到人性與心靈深處本質的探討:貞德能不能衝破人性的限制,把上帝賦予她的使命、跟她內心深處的童年創傷仇恨意識分開?
上帝給貞德的聲音只到查理加冕時為止。促使查理能加冕的大勝戰役,貞德差一點死掉。在出死入生之際,貞德夢見自己回到創傷的童年,英軍對姊姊說:「拿劍的女人!」將姊姊殺死強暴。
也就是查理加冕後,貞德漸漸忽略旗幟,最後連同僚的呼喊「旗幟!旗幟」也不聽,她手中只剩下劍,沒有旗幟了;她不知不覺的,將使命轉換成復仇。
這回到創傷的童年,大喊:「都是我的錯,是我太晚回家。我永不能原諒他們,為何她要為我死?為何祂要救我?」然後晚上偷偷回到教會,自己拿起聖杯飲下葡萄酒,鮮紅的酒汁像血般塗了半張臉,又流到身上。貞德舉杯向祭壇上的十字架說:「我現在就要跟你合一。」
在她內心深處,十字架是旗幟、也是劍,與上帝合一是神聖、也是血。
電影敘事中,貞德是在查理加冕後徹底的變了。
在獄中貞德孤立無援,恰像在曠野中的耶穌。黑衣人讓聖女貞德遭逢的,也是企圖讓她全盤否認使命。黑衣人切中要害:劍不是來自神蹟(使命不是來自上帝)。黑衣人告訴貞德,妳只是選擇自己要看的,那不是神蹟。
神蹟一推翻,因神蹟而來的使命也被推翻,儘管黑衣人從未要貞德否認上帝(撒旦試探耶穌時也從不否認上帝)。盧貝松刻畫的貞德,沒有德萊葉電影裡的貞德那般幸運,看見「上帝要我透過殉道得到大勝利。」她與上帝之間的關係立刻一無所憑,自幼便一直想跟上帝永遠同在的信念,如今是一無所有,貞德這一生墮入徹底的虛無與荒謬;所以貞德火刑死時,表情是如此的恐懼,這是多麼可怕的死亡前的徹底的拆毀。
 <==>
<==>
比較德萊葉的「聖女貞德」,貞德死前告訴那個相信她的主教:「上帝給我的大勝利,是透過殉道而得。」則德萊葉上火柱的貞德是掌握住「使命與十字架」的核心奧秘的聖女;盧貝松上火柱的貞德,是曾依隨上帝聲音而行,最後緊緊被童年創傷下的復仇意識擄獲,扭曲十字架使命真義的凡人。
因循這邏輯敘事,對於歷史上的記載,貞德曾簽名承認自己乃受魔鬼引誘帶領作戰、而後又翻供一事,盧貝松將之解釋為貞德太渴望領聖杯與上帝合一,因而做出的妥協。
● 黑衣人到底是什麼含意?
最後,我們要探討盧貝松電影中最後出現的黑衣人。
黑衣人到底是誰?是上帝?還是魔鬼?當貞德問黑衣人:「你是誰?」黑衣人將自己變成童年貞德看到的「祂」、長成後看到的「祂」、最後又變回黑衣人自身,然後問:「有何差別?」這與電影一開始神父對小貞德的回答:「無論祂來自哪裡,應當是好的。」頭尾呼應。

我們發現黑衣人將信仰變成心理學的意義,將不可言說的神秘體驗徹底理性化,他其實是另一個「劍」與「十字架」,當他幫助貞德自省時,他是十字架,但是讓貞德走上徹底的意義的相謬與虛無,他卻成為劍。黑衣人在幫助貞德自省更認識自我時,同時也徹底拆毀了她。
對於貞德的使命到查理加冕為止;從此要靠「一粒麥子死了,便生出許多子粒」這上帝使命背後的更大的神蹟奧秘,理性的黑衣人沒有能力讓貞德參透。
黑衣人豈不是在很多信仰追尋者的心靈中永恆的活著,既成為十字架,也成為劍?黑衣人,豈不正是二十世紀以來越來越走入荒謬與虛無的時代成因?還有什麼方式,比黑衣人更能毀壞信仰呢?
於是分析黑衣人,我們會看到1999的「聖女貞德」,的確比1928的「聖女貞德」,更關注到一個屬於我們這時代的宏大視野。每一個觀眾在選擇認同黑衣人或反對黑衣人,也呈現觀眾自身的信仰抉擇!
(END)